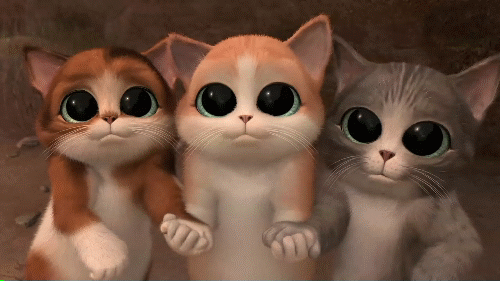![]()
9月,中国大学新的学年又开始了,几百万新大学生入学了。在这同时,中国的高考公平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话题。
专家说,高考制度存在地域歧视,对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有更多优待,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自由流动和考生的发展,是造成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知名大学大多集中于富裕地区,在高考名额分配限制下,欠发达省份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难度更大。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在辽宁省丹东出生长大,1980年考进北京大学,全辽宁省当年只有几十个配额。进了北大后,他和来自各省各市的同学们聊起高考分数,发现大家的分数都很接近,唯独北京的同学例外。
谢田说:“家在北京的学生,他们分数比我们低得非常非常多,多到我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有点愤怒了。我们要费很多很大劲儿才能进来,他们实际上很容易就进来了,他们那个分数要是在其他省份的话,绝对不可能上北大。”
“高考制度肯定是有地域歧视的,”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真正全面开放,按分数来的话,福建广东江浙这些地方的考生可能会占相当大的份额,而北京当地的一些学生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高考制度优待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谢田说,中国的高考制度显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省级省会城市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资源是三四线城市难以想象的,自己过去在丹东的教育资源和发达地区相比“差得太多了”,不同地区学生的质量和教育水平有很大区别。此外,发达省份拥有更多好大学,这些学校又为本地生保留大量名额,其他省份的考生只能挤破头争夺各省分配到的稀少名额。而在开学后,本地生和外地尖子生之间的程度立见高下,在学习程度上有落差。
谢田指出,中国官方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的照顾明显较多。这些地方有更多共产党高官子弟,他们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北大清华,甚至在过去还能利用家庭优势保送。当年在北大就有许多保送入学的红二代,学期成绩明显落后于来自其他省份的学生。
而现在由于名额分配制度,大城市的“皇亲国戚”也相对容易上好学校,共产党实际上在加大阶级之间的差距。相反的,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不被认为是当地的人,子女的教育、入学入托都成为问题。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重的,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做得非常完善,号称是共产主义均贫富,实际上更加清晰地把人区别成三六九等,并且每一级的工资待遇、福利、退休金、医疗保险都非常不同。户籍制度维持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也非常严重,”谢田说。
高考名额分配的争议实际上与户籍制度有关,谢田表示,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以成绩择优录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户籍制度,这是中共所不乐见的。“中共当时为了控制人民,尤其是控制农民,然后也控制人口的流动,使用了非常恶劣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没有这样的限制。
户籍制度便于他的统治监控,按县按区把人划分固定,等于是画地为牢,”他说,高考按照地区来分配录取名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为了维护政权的统治,通过户籍把人们固定在所在地,不给人们自由迁徙和流动的空间。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而它又不完全开放全国范围内自由竞争,这对大学来说也不是好的,它没办法拿到最优秀的人才,”谢田说。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对美国之音说,高考名额分配制度和重点大学分布不均,实际上是针对经济效益和政治的歧视。例如在北京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学校,其直接领导者是中央政府,他们的子弟居住在北京市,自然要给北京市相当的名额照顾职工子弟。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的孩子比农村孩子更聪明,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地方的孩子更有见识,前途发展也更好,尽管听上去类似于狡辩,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2001年,三名山东青岛考生起诉中国教育部,控诉高考全国试题相同但各地录取分数线不同是“教育歧视”,例如北京重点本科的的录取分数线为454分,然而这三名考生所在的山东省分数线却是580分,原因正是中国针对各省市高校招生数量的名额分配制度,导致一所学校录取的分数线可能相差一两百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诉讼流程“不合规”为由不受理此案。
这起事件后,2002年起,许多省份开始采取高考单独命题,不再是全国共用一份考题。郑旭光表示,各省独立命题的做法对公平性毫无改变,目的只是为了减少人们过去对于分数线差异的明显观感。
各个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人数已经确定,那么不论是哪一份考题,每年能进到这些大学的学生都是定数,区别只在于各省单独命题后,外界就没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分数线。
“各自出题你就没法攻击了,把这个攻击点就消灭掉了。但实际上并不增加公平性,因为各个高校在各个地区的名额并不因此增加或者减少。各地出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地域上的争吵,”郑旭光说。
农村孩子的难题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联席主任李宏彬1972年出生于吉林,他说,自己小时候根本没想过要读大学,周围也没有这样的风气,当时中国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和现在有很大差距。
“我出生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什么教育。然后我1978年上了小学,中国刚刚恢复教育。所以我读书那时候,学校里老师都没有,因为文革十年没有大学生,中国没人从事教育,”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并不是读大学找工作,最好的工作都是去一个好的国有企业,去一个厂里工作,接父母的班,这是那代年轻人小时候的理想。”。
在李宏彬长大的七十年代,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变大,社会对教育的观感逐渐改变,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在以前的国有企业,读不读大学收入没有差别,后来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收入差距慢慢变大,这种现象激励了读书风气,因为“读书有好处”,会让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一直持续到今天,城市的孩子基本预期都要上大学,农村可能一半人上大学,而在贫困地区比例更为悬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贫困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均,李宏彬表示,家庭观念是最大因素,从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以及给孩子的预期,都会影响孩子受教育的情况。学校环境也是重要原因,李宏彬刚从一个中国贫困农村考察回来,当地新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学,然而里头没有师资。
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其实不差,困难的是聘请好的老师。贫困地区留不住好的老师,他们在城市里有更多机会,造成农村学校硬件很好但软件不佳的约束条件。
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是一个原因,对农村孩子来说,读书的成本不低,但是预期的收益可能很低,这些家庭自然不愿意在教育上投资。相对来说,城市的富裕家庭重视教育,家长除了选择好学校,还愿意在课外辅导上花费很多时间和投资。即使中国当局自2021年实施了打击补习机构的“双减政策”,这种辅导转变为以零散形式出现的家教模式,价格也因为变成很多小的单位而提高。这种情况下,精英家庭仍处于优势。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所处环境最卷的一群人,家长为他们请家教和报名培训,一定要孩子上大学。穷寒家庭对孩子则没有那么多期待,如果表现并非特别出色,不如早点就业挣钱。不同阶层的家长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不同,子女的未来因而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放开户籍制度以解决高考争议难度大中国的精英大学集中在富裕地区,大多位于沿海城市。2016年,中国教育部试图安排14万录取名额给贫困地区考生,大约占考生总数的6.5%。由于要求学校减少本地招生以腾出名额,引发了城市里家长的抗议。
中国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中,北京占25所,上海8所,江苏和湖北皆为7所,陕西5所,四川4所。人口约一亿人的河南则一所都无。这些高校倾向于对本地生开放更多名额,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约为10%,但由于好大学众多,足以满足当地学生需求。上海、江苏和湖北的本地生比例也接近45%。
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说,高考录取名额分配的问题非常难解决,因为规则已定,任何调整都会是零和游戏。重新分配名额固然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但同时也影响其他省份的利益,而且大学的资金来源很多来自本地的财政和税收。
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有没有可能逐渐放开户籍政策,让考生可以跨省去参加高考,农村孩子更容易进城去读书,或者全国统一高考。当然这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政策本身也会改变利益。”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在中国,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同时存在。在“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高校资源非常少,有些省人口却将近一亿,这些考生的机会比发达省份的考生要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成为“高考移民”,为了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迁移到招收分比较低的地区。但大部分家庭很难采取这种做法,而一旦调整高考制度将会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国当局不会愿意得罪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家长。
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师大多不愿意去到农村,郑旭光认为如果要讲求教育公平,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资金,突出贫困地区的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且取消户籍政策,让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有机会将户口迁到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地区。
“中国政府收了那么多的钱进行转移支付,就应该对中西部落后或穷困地区优先投入教育,而且要比东部实际的教育投入更高,才能够达到教育平等。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掏这个钱,对于大学培养精英和提升全民基本素质来讲,不能用刀下见菜的市场原则来进行,”郑旭光说。
中国从科举到现在的高考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周围国家如韩国的竞争也极其激烈,
李宏彬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若改动高考制度,一时之间也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但这个制度走到极端可能造成阶级固化,富裕阶层永远富裕,贫困家庭也继续复制上一代的条件。
最后还是回归到收入分配问题,在欧洲、日本情况相对好一些,他举例,日本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卡车司机的工资虽有差异但不是太大,但到了中国和美国差异却相当悬殊。由于存在工作收入的差距,如果通过上大学能改变差距,人们会非常愿意努力投资于大学教育,这样的情况下,有资源和资源稀缺的家庭结果就会不一样。
福利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赞(73)